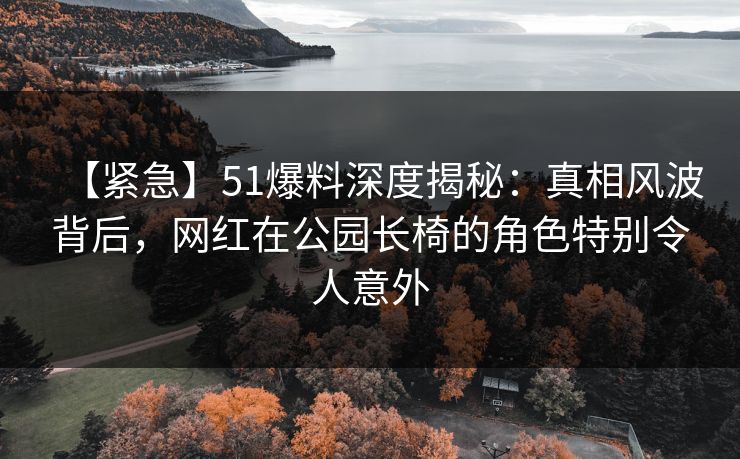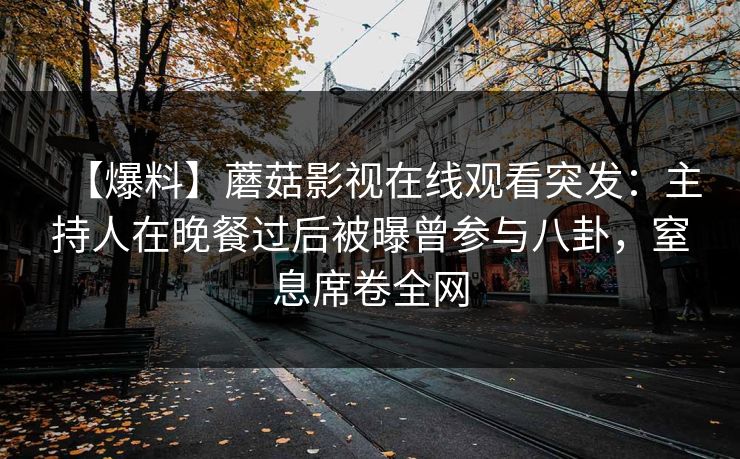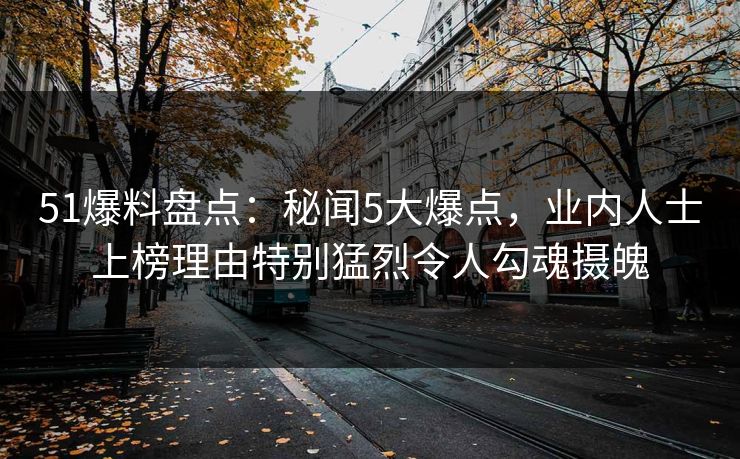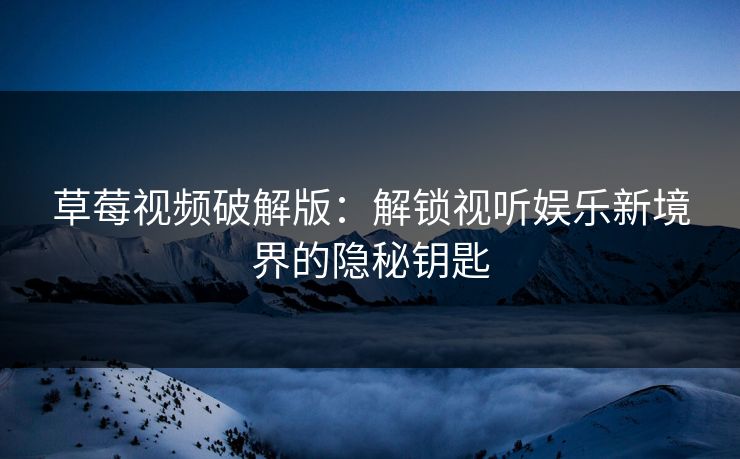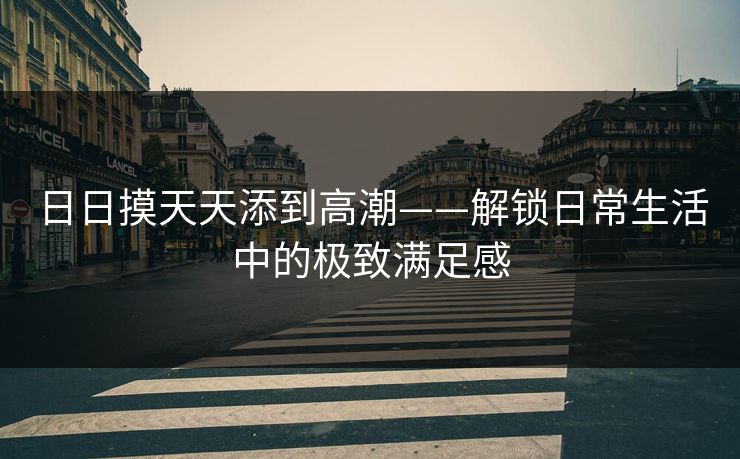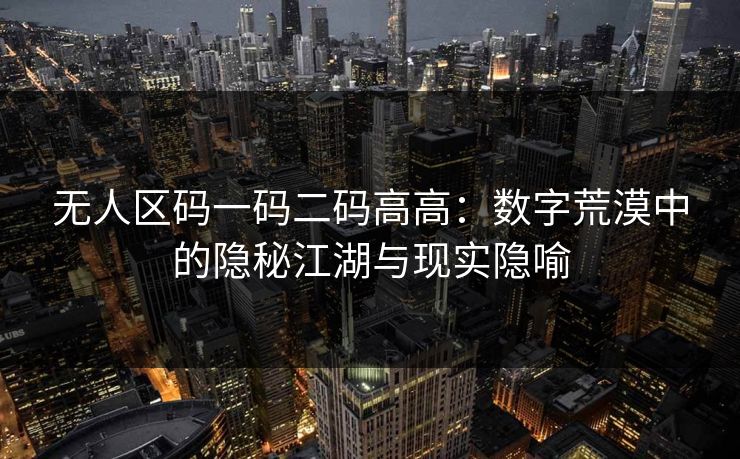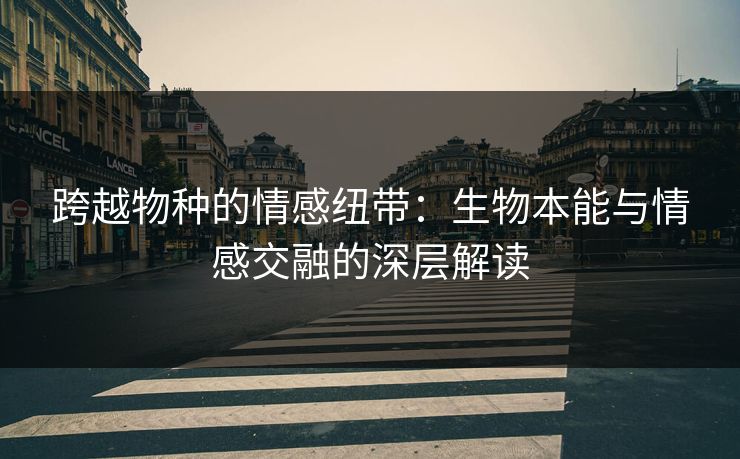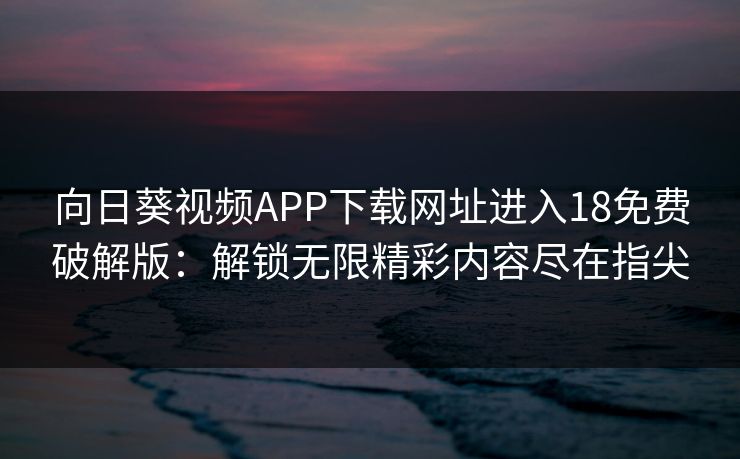从工具到伙伴:西方动物观的千年蜕变
在古罗马斗兽场的沙地上,狮吼与人群的欢呼交织,血液渗入土壤。这是公元1世纪的欧洲——动物是工具、猎物或象征权力的展品。亚里士多德在《动物志》中冷静分类生物等级,中世纪猎鹰成为贵族专属符号,而工业革命时期的拉货马匹终日困于阴暗巷道…西方文明与动物的关系,曾长期停留在“利用与被利用”的框架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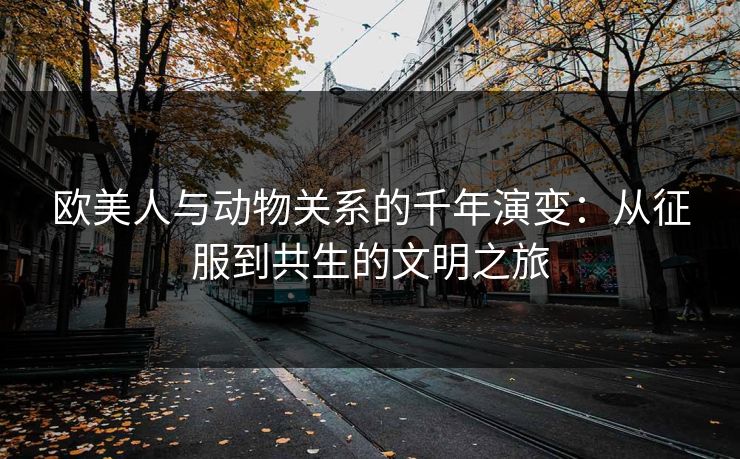
转折发生在18世纪。英国哲学家边沁掷地有声地追问:“问题不在于它们能否思考,而在于它们是否感到痛苦?”这句质疑撕开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裂缝。与此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湖畔歌颂云雀的自由,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中将人类重新放回生物谱系。动物不再是冰冷的“它”,而是能与人类共享地球命运的生命体。
19世纪动物保护立法浪潮席卷欧美:英国1822年颁布《马丁法案》禁止虐待牲畜,美国1866年成立防止虐待动物协会(ASPCA)。这些变革背后,是哲学、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共振。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开始将宠物犬抱入怀中拍摄肖像照,德国画家马尔克用绚烂蓝色描绘奔腾的马群——动物逐渐从功能性存在升华为情感与艺术的载体。
20世纪的实验室里,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金纳用鸽子探索行为主义,却也引发动物伦理大辩论;迪士尼的《小鹿斑比》让数百万观众为森林生灵落泪。这种矛盾与共情并存的张力,恰恰折射出西方社会动物观的成熟:既承认人类需求,也反思自身责任。至1975年彼得·辛格《动物解放》出版,一场从餐桌到化妆品柜台的伦理革命悄然启幕。
共生时代:当动物成为家庭与生态的联结者
21世纪的纽约公寓里,金毛犬拥有专属智能喂食器;伦敦街头随处可见“宠物友好”咖啡馆标签;柏林动物园为北极熊建造仿冰川栖息地。欧美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物关系升级:从“保护”迈向“共生”。数据显示,67%的欧美家庭至少饲养一只宠物,每年动物福利捐款超百亿美元。
这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迁,更是文明内核的重塑。
社交媒体加速了这场变革。Instagram上柯基犬账号拥有百万粉丝,YouTube动物救援视频年播放量破百亿次。数字时代打破了物种间的信息壁垒,一只被遗弃小猫的遭遇能瞬间引发全球声援。这种“云养宠”现象背后,是技术赋能的情感联结——动物不再是遥远他者,而是触手可及的家庭成员。
生态意识的觉醒进一步重构了人与动物的空间关系。挪威“野生动物桥梁”让麋鹿安全穿越公路,加拿大禁止圈养鲸类,荷兰出现全球首个“动物政党”。这些实践将动物权益纳入城市规划、法律体系甚至政治议程,标志着共生理念从个体情感升维至社会治理。
但挑战依然存在:工业化养殖与动物权利的矛盾,流浪动物收容系统的资源困境,野生动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…欧美社会用科技与伦理并进的方式回应着这些难题:人造肉技术减少屠宰需求,AI芯片监测濒危物种迁徙,动物行为学研究成果被写入法律草案。
或许正如生物学家古道尔所言:“我们与动物共享的不是星球,而是生命本身。”从斗兽场的血腥到客厅的拥抱,从征服到共生,这段跨越千年的关系演变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侧写,更是一面映照自身人性的镜子——当我们学会与其他生命温柔共处,我们才真正成为了完整的人。